今天读了一下著名的《方方日记》。读了之后发现这本书其实算不上是书,而是一本以日记为名的小说。从内容上来说,其实算不上有什么逆天的错误,因为作为小说,本来也不需要详实地调查和严密的论证。说到底,它只是方方在疫情严重的武汉,在恐慌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急切地发了些牢骚而已。在这种情形下,无论是她写了啥都没有必要太当真。毕竟她作为一个作家,除了文字功夫,对于社会治理和传染病学,生物学懂的其实并不多,对整件事情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口耳相传和脑补。
一个什么都不太懂,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话很重要的人,是很容易写出方方日记这种文本的。这种人在社会上其实很寻常。比如说,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就很爱聊他们并不懂的国家治理和外交事务。这种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害人之心,只是如果写的东西有问题,看的人又信了,那就会造成问题。这也是所有公知的通病:懂得太少,写的太多,名声太大,德不配位。如果他们都去当出租车司机,至少还可以为社会做点实质性的贡献,为人民的交通提供一些便捷。但是他们因为文采太好,名声太盛,仅凭想象写点东西就可以获得财富和地位,那是不可能有动机去做实质性贡献的。
方方就是一个文字功夫很强的人。作为专业小说作家,写的东西感情很丰富,适合传播。而且每天都写,整理成册。在微博这种散兵游勇键盘侠的集散地,方方可以说就是一枝独秀,想不出名都难。更何况,物以稀为贵,即使是一坨屎,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吹捧而且足够稀缺,也能成为名贵的“猫屎咖啡”
互联网舆论,总是需要一个搞批斗的理由贬低别人抬高自己,左和右都在搞一些“抛开事实不谈”谈“大是大非”的事情,方方也不例外。方方日记通过专业机构在海外火速出版,而且发售的广告上说这个是“中国禁书”(显然不是,百度随便一搜就能读到)。这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不畏强权恐吓的勇敢自由战士。中国的敌对势力最喜欢这种东西了。自然有国民对这种行为很不爽:方方在疫情期间作为一个领导本来是有责任做些实事的,作为一个上流阶层的人是可以捐点东西的,结果躲在家里没有帮上任何忙,享受了官僚特权,还要把全城人民的痛苦经历用来卖钱,而且是卖给武汉人民的敌人。这样一来,方方就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汉奸走狗。再后来,方方接受了BBC的采访,更是宣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和政府搞对立,就更加的覆水难收,彻底的背上了汉奸的帽子。
到这一步,方方日记就已经脱离了文字本身,而是成了一种“公知卖国求荣”的意象,升级成了意识形态斗争。方方也成了一个集合了官僚,发不义之财,自私自利,卖国求荣等负面标签的综合体,而方方本人和支持者给自己的标签“不畏强权恐吓的勇敢自由战士”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。假如方方真正去做详实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证,在出版一事上征求武汉人民的同意,她的财富和地位也就没了。毕竟她是一个平庸的作家,而这部方方日记是她知名度最高的作品。
公知大抵如此。一个“公”字表示知名度高,一个“知”字表示说很多话。可惜人们以为“公”是指公共事业,“知”是指知识。公知以舆论为事业,活在自己的狭小认知里,一遇挫折就摆出一副“言论不自由”,“说真话被迫害”的受害者姿态,刚好又可以以此为题又拨弄一番言论迎合支持者的认知,创造业务增长点。这样的工作并不对社会真正有益,只是让支持者花钱听胡诌获得高人一等的感觉,让反对者心情很差然后通过批判公知也获得高人一等的感觉,而且无论支持还是反对,只要有讨论就有名声,有名声就有地位和财富。当整个业务逻辑能跑通,但是又不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,公知就不可避免的反动了。
那么如何避免成为反动的公知呢?唯有谨言慎行,勤学好问,少一些臆想和脑补,多一些实践和考察。文采再好,只应服务与事实和逻辑。名声再旺,只应先好好做人。如果回归到公共事务和知识上,做一个公知是不会反动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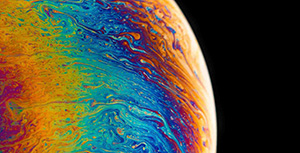


评论区